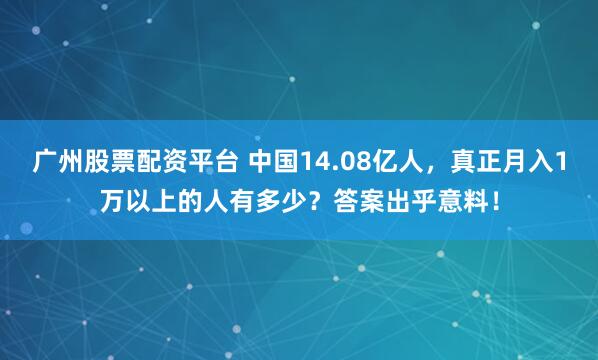
暮色像掺了温水的墨汁,慢悠悠地在天边晕开,把巷子口的老槐树染成了深褐色。街灯像是守着老规矩的伙计,顺着青石板路从东头到西头次第亮起,昏黄的光落在凹凸不平的石板上广州股票配资平台,映出细碎的光斑,倒添了几分暖意。巷口老王头的烤红薯摊,跟这暮色似的准时 —— 铁皮桶刷得锃亮,里头的炭火正旺,红通通的火苗裹着红薯的甜香往上窜,那股子焦甜劲儿能飘到巷子尽头,勾得放学的娃、下班的人忍不住往这边多瞅两眼。
老王头的手糙得厉害,指节粗大,虎口处还留着年轻时在厂里干活的疤痕,跟老树皮似的,可翻弄红薯时却格外轻。他用铁钩子把桶里的红薯挨个翻了圈,红薯皮烤得发焦,裂开的缝里渗出琥珀色的糖汁,滴在炭火上 “滋啦” 响。正琢磨着今晚能卖多少斤,脑子里突然蹦出今早收音机里的话 —— 主持人说现在 “月薪过万” 的人不算少,还提了一嘴二十年前的 “万元户”。老王头忍不住 “嗤” 了声,手里的铁钩子顿了顿:“这词儿搁以前,那可是能让全村人围着眼馋的稀罕物,现在倒好,跟唠谁家今晚吃了面条似的平常。”
展开剩余87%风里裹着点凉意,老王头裹了裹身上的旧棉袄,想起前阵子在菜市场听人说的统计局数字 —— 全国十四亿人里,能月入过万的还不到八百万。他没念过多少书,算不清这数占了多少比例,只觉得跟自家桶里的红薯似的,看着一堆,真要挑出个头大、糖分足的,没几个。这银钱事儿啊,就跟这暮色里的光影似的,看着暖,细琢磨起来,满是说不透的滋味。
一、铁屋里的新梦:从 “万元户” 到 “月薪过万”,银钱的 “分量” 咋变了?
老王头总爱跟来买红薯的老街坊唠旧事。他常说,二十年前要是谁家成了 “万元户”,那可比现在中了彩票还风光。“那时候我在国营厂当工人,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多块。村东头的老李,靠养猪卖猪攒下了一万块,县报记者都来拍照,村里广播天天念他的名字,连我家娃都吵着要去老李家门口看‘万元户的房子’。”
可现在呢?“月薪过万” 成了街头巷尾常听见的词。傍晚在公园下棋的老头,凑一块儿能聊 “我家小子在互联网公司,一个月挣一万二,就是天天加班”;菜市场买菜的大妈,跟摊主砍价时都能提一嘴 “我闺女当老师,月入过万,也不缺这几毛钱”。老王头总觉得纳闷:“这钱咋好像越变越‘不值钱’了?以前一万块能盖个砖瓦房,现在月薪一万,在城里租个带阳台的房子都得花掉小一半。”
他还注意到,现在年轻人嘴里的 “钱事儿”,他越来越听不懂了。银行门口穿西装的年轻后生,跟客户说话时总蹦 “期权”“基金定投”“股票 K 线”,那神情跟以前茶馆里说《三国》的先生似的,唾沫星子横飞,听得人云里雾里。有回邻居家的小伙子来买红薯,说自己在 “搞理财”,老王头问他 “理财是啥?跟以前存银行有啥不一样?”,小伙子解释了半天,他还是没弄明白 —— 只知道这些新词儿,都跟 “怎么能多挣钱” 绕不开关系。
更让老王头咋舌的是 “地段里的钱味儿”。他听去北京带孙子的老伙计说,京城金融街周边的早点摊,豆浆都比别处贵五毛。“摊主说‘旁边写字楼的人,早上买豆浆都不砍价,涨五毛算啥’。” 老王头摇摇头:“你说这事儿,真是‘人跟着钱走,钱跟着热闹走’。那些能挣大钱的地界儿,连喝碗豆浆都得多掏钱,咱这小老百姓,只能在旁边瞅着。”
二、数字里的阴阳面:月入过万的人,咋跟撒在湖里的盐似的?
有回老王头去社区办事,墙上贴的宣传海报里写着 “全国月入过万人数约 784 万”。他凑跟前看了半天,心里算了笔账:“全国十四亿人,784 万搁里头,不就跟往洞庭湖撒把盐似的?压根显不出啥来。” 后来他又听人说,月入两万的人更少,全国也就一百来万,“那更是跟过年时天上的烟花似的,少见得很”。
最让他觉得 “邪乎” 的是,这些能挣大钱的人,还爱 “扎堆儿”。去上海旅游的孙子跟他说,陆家嘴的高楼里,随便进一家公司,里头不少人都是月入过万;深圳南山的科技园更厉害,刚毕业的大学生,要是会编程,一个月就能挣一万多。“可咱老家镇上呢?” 老王头叹了口气,“我侄子在镇上的五金店当伙计,一个月挣三千五,都觉得是‘体面活儿’,能挣五千的,那都是店里的老师傅,得有十年以上的手艺。”
他还想起去年回老家的事儿。村里的二柱子在深圳打工,过年回来跟乡亲们唠嗑,说自己在南山的电子厂上班,一个月挣八千,“不算多,厂里好多技术员都能挣一万二”。可二柱子的媳妇在村里的小卖部当收银员,一个月才一千八,“连给娃买奶粉都得算计着来”。老王头说:“这世道就跟老辈人说的‘旱的旱死,涝的涝死’,钱这东西,就爱往高楼多、年轻人多的地方跑,小地方想留都留不住。”
有回卖红薯时,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跟老王头抱怨:“叔,我在互联网公司月入一万五,看着不少吧?可房租一个月四千五,通勤费两百,吃饭两千,再加上水电费、物业费,一个月下来能存五千就不错了。我老家在县城的同学,月入四千,住家里不用交房租,吃饭跟爸妈一起,一个月能存三千,比我还踏实。” 老王头听了这话,更糊涂了:“这钱挣得多,花得也多,到底啥样才算‘有钱’啊?”
三、朱门内外的分野:会洋文、懂机器,真能多挣钱?
老王头年轻时候,村里最有出息的是能 “扛活” 的壮汉 —— 谁家盖房子、收庄稼,都愿意找力气大的,一天能多挣两毛钱。可现在不一样了,他听孙子说,现在找工作,“会洋文、懂机器” 的最吃香。“我孙子在大学里学‘计算机’,说毕业以后能去‘互联网公司’,一个月能挣一万多,抵得上我以前在厂里干大半年的工资。”
他还听说,京西的科技园里,那些搞 “编程” 的年轻人,不少都是刚毕业就能拿高薪。有回邻居家的小芳,大学毕业去了北京的一家 “科技公司”,一个月挣一万二,刚开始还跟家里炫耀:“以后能给爸妈买新衣服了。” 可没过仨月,就跟家里诉苦:“房租一个月四千,吃饭一个月两千五,公司楼下的奶茶都要二十块一杯,再买点护肤品,一个月下来根本存不下钱。”
老王头这才明白,“挣钱多” 跟 “过得好”,压根不是一回事。他想起自己在老家的日子:房子是自己盖的,不用交房租;院里种着白菜、萝卜,不用花钱买;头疼脑热的,去村里的卫生所拿点药,花不了几块钱。“我一个月卖红薯能挣三千多,除了买点煤、交点电费,剩下的都能存起来。可城里那些月入过万的年轻人,看似挣得多,其实跟‘给房东打工’似的,手里的钱还没我踏实。”
更让他感慨的是 “学问里的钱”。以前村里的先生总说 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他还觉得是哄小孩的话,现在才知道这话不假。“我邻居家的小子,以前不爱上学,初中毕业就去工地干活,一个月挣五千,天天风吹日晒的;他弟弟爱读书,考上了重点大学,学‘外语’,现在在上海当‘翻译’,一个月挣一万五,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。” 老王头说:“这世道变了,以前靠力气挣钱,现在靠脑子挣钱,没学问,连挣钱的门儿都摸不着。”
四、新式算盘:月入过万,咋还跟以前算计粮票似的?
老王头家里还留着一个旧算盘,是他父亲传下来的,木头框子都磨得发亮。他总说,以前过日子靠算盘,现在过日子靠 “算计”,不管挣多挣少,都得精打细算。“以前我妈拿着粮票买米,一斤粮票能买多少米,都得算得明明白白;现在城里那些月入过万的人,过日子也一样 —— 房租多少、吃饭多少、人情往来多少,都得一笔一笔记着,生怕超了预算。”
他听去城里带孙子的老伙计说,现在的年轻人,连买棵白菜都要 “货比三家”。“我老伙计的儿媳妇,在公司当‘经理’,一个月挣两万多,可去菜市场买菜,还跟摊主砍价‘这白菜能不能便宜一毛钱’;给孩子买衣服,专等‘打折’的时候买,说‘能省一点是一点’。” 老王头笑了:“这不跟以前咱算计粮票一个样吗?以前是‘粮票不够用’,现在是‘钱不够花’,过日子的心思,从来没变过。”
邻家阿二的事儿,更让老王头觉得 “钱经难念”。阿二在码头扛了十年活,以前总说 “钱是王八蛋,花完再去赚”,可自从儿子去城里工作,他就变了。“他儿子在城里当‘设计师’,月入一万二,阿二刚开始挺高兴,说‘以后不用愁养老了’。结果没过多久,阿二就开始愁 —— 儿子说要在城里买房,首付得好几百万,就算一个月存五千,也得存几十年。” 老王头说:“你看,就算月入过万,遇上买房、结婚这种大事,照样得犯愁,跟以前咱愁‘盖房子没钱买砖’,没啥两样。”
有回卖红薯到半夜,老王头看见写字楼里还亮着灯,窗户里的人影来来往往。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候在厂里加班,也是这样,为了多挣点加班费,能熬到后半夜。“以前加班是为了‘攒钱盖房子’,现在年轻人加班是为了‘攒钱付房贷’;以前省吃俭用是为了‘给娃交学费’,现在省吃俭用是为了‘给娃报兴趣班’。” 老王头叹了口气:“这世道变了,可老百姓为钱奔忙的劲儿,从来没变过。”
五、暮色里的念想:奔着钱去,别丢了心头的灯
铁皮桶里的炭火渐渐弱了,红薯卖得差不多了,只剩下几个个头小的,躺在桶底冒着热气。老王头收拾着摊子,把铁钩子、秤杆放进旧布包里,抬头望了望远处的写字楼 —— 那些窗户亮着灯,一个个方方正正的,在夜色里看着,竟像极了一个个小小的 “钱眼”,吸引着人们往里钻。
他想起自己卖红薯的这些年,挣的都是 “辛苦钱”—— 天不亮就去批发市场挑红薯,回来洗干净、烤透,一站就是一整天,冬天冻得手发麻,夏天热得满身汗。可他觉得踏实:“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烤出来的,花着心里有底。” 有回一个年轻人跟他说 “叔,你这生意挣不了大钱,不如去开个网店”,老王头笑了:“我没那学问,也没那心思,卖红薯挺好,能看着街坊邻居的笑脸,还能挣点养家的钱。”
他总跟来买红薯的年轻人说:“挣钱是好事,可别为了挣钱把身子熬垮了,也别为了挣钱忘了家里人。” 有回一个小伙子跟他抱怨 “天天加班到半夜,跟女朋友都没时间见面”,老王头劝他:“钱是挣不完的,可日子是过出来的。以前我在厂里加班,再忙也得回家陪娃吃饭,现在你再忙,也得抽时间跟女朋友唠唠嗑,别等钱挣着了,身边的人却没了。”
夜色越来越浓,巷子里的人少了,只有街灯还亮着,把老王头的影子拉得老长。他揣着今天挣的零钱,慢悠悠地往家走,口袋里的钱叮当作响,心里却格外踏实。他想起小时候,父亲跟他说 “日子就像烤红薯,得慢慢烤,才能烤出甜劲儿”,现在才明白,这银钱事儿也一样 —— 不用跟别人比,只要自己踏实肯干,心里有盼头,日子就能过得甜。
走到家门口,老王头看见屋里亮着灯,老伴正等着他吃饭。他推开门,一股饭菜香飘了过来,暖乎乎的,比烤红薯的香味还让人安心。他想:这世道不管怎么变,银钱不管怎么挣,最要紧的还是身边的人、心里的盼头。要是为了钱丢了这些,就算挣再多,日子也没啥滋味。
窗外的夜色更浓了,可屋里的灯亮着,把日子照得暖融融的。这银钱事儿啊广州股票配资平台,说到底,不过是为了这盏灯、这桌饭、这份踏实的小日子。
发布于:江西省启灯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